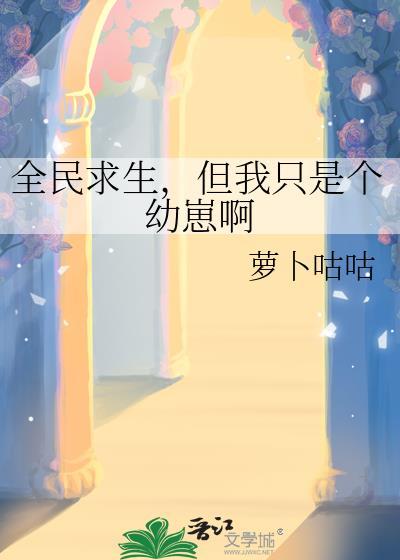零零电子书>帝师声泪俱下免费阅读 > 第74章(第1页)
第74章(第1页)
新的一年,知荷县前任县令升迁走了,新的县令来了,百姓们还是照常过日子。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急景流年,转瞬又到了年尾,温催玉在酒楼里做这账房先生也有一年半了。
还有三个多月,明年的三月十四,就是他离开雁安整整三年的日子。
这日他从酒楼回家的路上,被县尉叫住了,县尉后头还跟着两个衙役。
“哎,是崔先生,正好,我们准备去你家呢,在这儿遇上了,那要不就在这说吧。”县尉说。
温催玉不明所以,客气道:“好,是有什么事呢?”
县尉从衙役手里拿过一张告示,又递给温催玉:“别担心,不是坏事儿,就是跟崔先生通知一下这个消息。县上读书人不多,县令大人就让我挨家挨户都通知一下,免得谁两耳不闻窗外事给错过了。”
温催玉接过告示的纸张,一边看一边听县尉接着说。
“以前啊,这要当官,都要走举荐,得有大名声,但朝廷说明年开始,改成读书人凭考试封官,叫科举,就不举孝廉了,说是能更公正,让寒门子弟也多些机会。”县尉说。
“这也是咱们封地的主子琰王他生前留下的举措,所以和先前那新纸一样,也从咱们封地内的郡县开始推行,不过咱们封地太大,这种举措一次性全改有点动静太大,所以朝廷说是先改一半。”
“你猜怎么着?咱们知荷县就在这被改的一半里!”县尉指了指告示,“要考什么科目,什么时候考,都写上面了,你自己衡量衡量,要不要参加。要是想当官,最好是早点考,县令大人说,上头的意思是刚开始嘛,直接上雁安考就行,后面推行得久了,估摸着要多考好几道槛。”
温催玉收好告示,他自然是不会去考的,但他这会儿也没当面说“不识好歹”的话,只点点头笑道:“好,我知道了,多谢县尉大人特意跑这一趟来通知我,这是件要紧事,我一定好好记挂在心上。”
县尉跟两个衙役笑道:“瞧,我们走了几家,就崔先生听了之后最稳重,不像前头那几个,高兴得好像已经考上当了官似的,都乐得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跟县尉他们道别后,温催玉继续带着生姜回家。
回到私塾堂,又把告示拿出来看了看,温催玉有些欣慰地轻笑了下。
就他在知荷县接收到的消息来看,卫樾这个皇帝当得很是勤勉贤明,在民间的口碑也是越来越好。
不过桩桩件件,直至如今改动选官制度,卫樾必然殚精竭虑、付出了诸多辛劳,才能控制住朝局、顺利推行举措……也不知道他把自己照顾得好不好。
……
这年除夕宫宴之上,卫樾突然宣布,他准备南下巡视,在温太傅三年忌辰之际,到温太傅故乡西华郡去看看,正好西华郡也在琰国封地范围,他顺道逛逛温太傅的封地。
李丞相犹豫回禀:“陛下天子之躯,西华郡在琰国封地最南边,路途遥远……”
“朕当年北上去景国封地时,沿途更颠簸,可没见诸位这么关心。”卫樾随口道。
朝臣们:“……”当年摄政的赵曜把持朝政,他们也不是没人上谏过,没用啊!
好在他们陛下似乎只是随口一说,并没有借题发挥翻旧账、把人拉出来杖刑的意思。
“诸位既然担心朕,那就都跟朕南下罢,正好朕也不乐意让你们在雁安悠哉度日。”
卫樾接着如是说,听得朝臣们一噎、差点心梗。
“把处理政事需要的东西都带上,路上也别耽误了事情,三日后出发。朕意已决,谁还有意见,可以死谏。”
朝臣们:“……”
谁家皇帝见天督促朝臣死谏啊!
对于雁安朝廷从上到下的人而言,这又是一个过得愁眉苦脸的年。
宫宴结束后,朝臣们出宫回府。
大司农刚回府,还没喝上一口热茶,管家就递上来一封信:“大人,又是从陶潜郡来的信。”
大司农皱眉头:“真是过年都不让人清静!”
他看完了信,往屋内火盆里一丢:“这好侄子,真是会给他叔叔我添乱!我能有什么办法,谁让他不老实……早的时候不说,他要是早几年刚出事的时候说了,我还能帮他遮掩过去,现如今……陛下盯朝臣盯得死死的,有半点错就挨罚,错大点就去死,反正陛下不怕没人可用……我敢怎么帮他,我不要命的吗!”
管家是心腹,大司农说话也就不太遮掩,不然迟早要憋死。
听大司农这么说,管家作为知情人,安慰说:“大人,要老奴说啊,兴许是堂少爷他多虑了,不过是改成了科举考试而已,莫说还没有推行开,就是举国都推行了,也不一定就会挖出堂少爷他过去在别的郡县任官时犯的事儿啊。”
“可他就是怕啊。”大司农摇了摇头,“陶潜郡本来就刚出事没两年,从上到下清洗过一遍,他上次没被牵连,过去在别的地方的事也没被查出来,侥幸逃了过去,本来就战战兢兢,如今草木皆兵也不奇怪……”
一年多前,陶潜郡治下的清穹县县令犯事,被一个宫人告到了陛下跟前,连带着整个陶潜郡被大肆整顿了一番,陛下当时不计后果也要惩治滥官污吏的阵仗,至今叫官员们人人自危。
大司农叹气,又说:“别说,其实本官也怕,怕他的事被挑出来了,本官作为本家叔伯,在陛下那儿逃不了被牵连,陛下这脾气越来越难伺候了……唉,科举这事儿,真是让底下寒门有机会见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