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电子书>帝师声泪俱下免费阅读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没出温催玉和卫樾意料,果不其然,庄王虽然迟疑,但并未当即亲自前往白水山。
不过这也不妨碍他们行事。
翌日,初来雁安、想要出门游玩的卫淇主动到太傅府,跟卫樾和温催玉请了安,然后乖巧地问:“温太傅,我可不可以请你府上的子白和小七一起出门玩?我对雁安不熟悉,在这里熟识的同龄伙伴也只有他们两个。”
温催玉颔首:“当然可以,去吧。”
卫淇他们离开后不久,袁昭也来了——他因为一路护卫陛下、刚从景国回来,得了一段假日,眼下正闲。
一到温催玉和卫樾面前,袁昭便郑重其事地行了一大礼。
“采言一事,属下叩谢陛下、温太傅大恩。”袁昭说明缘由。
温催玉上前:“不必如此,快请起。”
卫樾则道:“这件事与朕无关,是老师他细心。”
温催玉无奈看了眼卫樾,又对袁昭道:“你不责怪我自作主张、越俎代庖便好。”
——此事要从早前说起,早到温催玉和卫樾甚至还没有前往景国的两年多以前。
那时袁昭刚投诚、教卫樾习武还不久,温催玉托了府上负责采买的静婶和钱婶,让她们特意多去袁家武馆所在的溪南街买东西,顺道打听打听先前小七打听出来的那些有关袁昭的流言蜚语的细节。
袁家武馆在溪南街几代经营,街坊邻居对他们家的陈年旧事多有了解。
会有此安排,一来是出于警惕、想要了解清楚,毕竟实话实说,那时即便是温催玉也还并不放心信任袁昭。
二来也是寻思着,袁昭投诚付出,虽然他自己说是为了赌前程、也谋一个报仇,他的启蒙夫子毕竟死于言语得罪了庄王,但就这么虚无缥缈的果子,吊在人前头就让人干活,旁的什么也不给,温催玉总觉得不踏实。
所以他便想着,若是此前探听得知的流言蜚语为真,说不定可以帮袁昭解一心事。
出乎温催玉意料的是,静婶和钱婶机缘巧合的,竟然直接跟袁家武馆的老板娘、袁昭他亲娘认识了,而且几位妇女十分投契,很快处成了好友。
在聊完了溪南街哪家的菜新鲜水灵、哪家的肉足称干净等等事宜后,有一天她们自然而然细说起了彼此的家事。
袁家就袁昭这么一个老大年纪的光棍儿子,袁母说起来,难免哀叹他不肯成婚的事,静婶和钱婶追问缘由,也是理所当然,并不突兀。
而对于袁母而言,自家家事不算什么说不得的秘闻,压根没多想,便坦白相告——
袁昭原本虽然没有亲事,但有个青梅竹马、交情甚笃的姑娘,正是他那启蒙夫子家的女儿文采言。两家其实也有些默契,想要等儿女年纪再大点,便定亲。
但袁昭十五那年,文夫子出了事,虽然没有祸及家人性命,但文家在雁安到底待不下去了。
文采言当年才十四岁,随着母亲,跟随文家大伯一家,离开雁安回了祖籍之地。
“说起来吧,现在我和我们家老头子也后悔,当年太怕事了,觉得文夫子毕竟是得罪了人,不想受牵连……我们家开武馆的,别人说起来都是什么性情中人、快意恩仇啊,但在雁安,真一股子江湖气,哪能安生过日子,是不是?所以我们当年送儿子去念书,本来是真不想让他再回来武馆。”
袁母当时如此说道:“但没想到,文夫子出了事,我们怕儿子继续当个读书人,以后被人翻扯出旧事来,万一说他和朝廷对着干……唉,还是让他回来习武了。”
“当年文家那姑娘要走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求我和他爹去提亲,说已经问过采言,她也愿意。好歹定了亲,采言和她娘就不必只能随文家大伯回老家,她们娘俩在雁安的住处又没被查封,还能住,我们家作为未来亲家再照顾些,也是名正言顺,而且她们娘俩又拖不了我们家什么。”
“现在想想,也确实是这么个理,但我和他爹怂啊,想着文家刚得罪了上头,我们家上赶着去结亲,知道的说我们两家是早有此意,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袁家武馆也不想干了呢……而且当时吧,我们也觉得儿子年纪不大,兴许过两年就忘了采言了。”
“所以就借口采言要给她爹守孝,说等她孝期过了,到时候文夫子的旧事也没人提了,我们就跑一趟文家的老家,去提亲。”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定亲就得光明正大,不然也留不下文采言母女。可他的父母当时不乐意,袁昭没办法,只得与文采言约定,三年后一定去接她和她娘回来。
但文采言母女俩回到老家的第二年,文家大伯便说,文夫子死得不光彩,文采言也就别守孝了,他作为文家之主,要把文采言嫁了。
文采言不愿如此稀里糊涂,但又别无他法,最后竟狠下心划破了自己的脸,顶着流了半张脸的血出现在下聘当堂。
此后,别说是文大伯原本安排的亲事告吹,便是其他亲事也难给文采言安排,毕竟文采言她爹死得本就忌讳,她又连一张好脸都没了。
而且文采言半脸血的模样被人茶余饭后传得血肉模糊、如恶鬼转世,除非文大伯连书香世家的最后一点脸面都不要、把这个侄女的亲事胡乱对付,不然他是嫁不出去文采言了。
而文大伯确实还稍微要点脸面,侄女嫁得太寒碜,他面上也过不去,但让文采言从此“高枕无忧”,他又觉得十分不舒坦。
于是,文大伯把文采言母女俩关在了一方小院里,不许她们再踏出门一步,对外宣称她们母女都疯了,而他作为文家当家人愿意养弟媳和侄女下半辈子,由此捞点所剩不多的名声。
雁安与文家老家相距甚远,又无人特意传递消息,所以袁家知道这件事时,早就尘埃落定了——他们是在文家离开雁安的三年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袁母说:“我和他爹本来寻思着,这小孩子时的情分,分开时间长了也就淡了,但没想到过了三年,我们家那个还是惦记着文家姑娘,时间还没到就催促我们操持。我们老两口便想着,那就办吧,既然儿子喜欢,也和人家姑娘约定好了,三年前我们当过一次恶人了,就不要再当一回了。”
“文家离得太远,我们两家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雁安本地的媒人不乐意跑那么远,所以我们是到了当地,现寻的媒人。”
没成想,那媒人一听是要对文家二房的姑娘文采言提亲,便忙不迭把前两年闹得满城风雨的事情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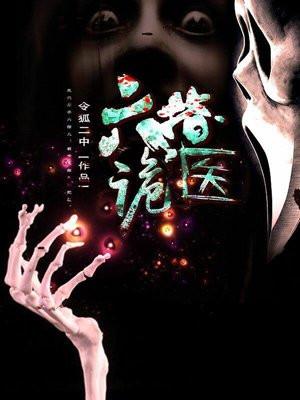

![无主之人[星际]](/img/2013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