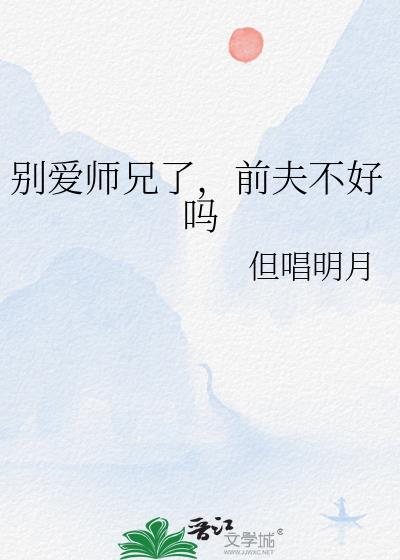零零电子书>丞相家的娇娘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现如今夫人要做的就是调养好身体尽快为爷诞下一子,而不是纠结身边是否多个人伺候,有些福该享就得享,而不是没苦硬吃。学那等自诩清高?不俗,却追名逐利之辈。”方嬷嬷连枪带棒的一句话,令玉荷的脸色刹那间变白,呼吸急促难以喘息。
也是,她只是一个典借的物件,如何?能对主人家?的命令指手画脚。
对方给的她只能接受,无论?是恩赐还是羞辱。谁让她只是一个被丈夫用一万两银子卖给他?的女人,
原先的谢府是在崔家?隔壁,但自此那日后便搬到了非富即贵的城东,同县令一家?相邻而居。
浑浑噩噩中回到谢府的玉荷远远地瞧见立在檐下的男人。
疏疏竹影,难拓君子三分?风骨。
可就是这样一副令人挑不出半分?瑕疵,称得上?琢玉公子的皮相,内里藏的皆是道貌岸然。
指腹下意识摩挲的谢钧随意扫向?她,言语清浅得似话家?常,“我听说你去崔家?了,是舍不得你那个窝囊废一样的丈夫吗。”
指甲往里蜷缩掐进掌心的玉荷唇角泛起一抹讥讽:“谢公子,我们只是交易的关系,难道你连不是自己?的物品去留归宿也那么在意吗。”
“你也说了,既是物品,就应该有做好一个物品的本分?。”谢钧高?大?挺拔的身影逼近她,遮住了她前头的日光,也拢住了在他?面前显得过于娇小的自己?。
“看?来夫人是休息好了。”谢钧被她口中的交易给气?笑了,果真她并没有外表所表现出来的温柔,反倒是倔强,带刺的。
而这不正是他?一开始看?上?她的理由吗。
想要摧毁她的清高?,打断她的傲骨,看?着她在自己?身下哭泣得溃不成军,又如午夜芍药独自绽放。
闻言,面上?血色尽失的玉荷想到那晚上?毫不节制的男人,竟是拔腿就要往后跑。
要是再来一次,她一定会死在床上?的。
她不要,绝对不要。
她正要逃离,谢钧已是长臂一搂勾入怀中,冰冷的唇贴上?女人圆润小巧的耳边,“我倒是不知崔夫人癖好如此特殊,喜欢以天为床以地为被。”
腰肢被禁锢住的玉荷脸色煞白,单薄的身体止不住轻颤,“我没有,还有你放开我。”
“你要是继续挣扎,我很难保证不会引得其?她丫鬟婆子过来围观。”谢钧弯下腰,以齿咬开她的外衫,露出她的素色中衣,微凉的吻落在她脖间小痣上?,“到时候我可不敢保证,会引入旁人目睹夫人玉梯横成之态。”
男人生得面如冠玉,潇潇月下影,偏生说出口的话粗俗不堪得连路边乞儿还要不耻。
抗拒着男人亲吻的玉荷身体虽僵硬却不敢推开,唯有死咬着唇不让自己?发?出半丝声响,生怕会引来其?她人。
虽只接触过短暂的几回,玉荷已然摸出了这个男人的性格。
高?高?在上?得不允许任何?人忤逆他?,从他?的谈吐举止中能看?出他?有着绝对的权势地位支撑着他?的傲慢,狂妄。
如今唯一能支撑着她的,唯有尽快怀上?他?的孩子,等孩子落地后一切就都结束了。
男人虽说着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依旧将人抱进了屋内。
很快,屋内就响起了令人面红耳赤的低声安抚,泣声连连。
直到此时,玉荷还坚信着只要怀上?后,一切都能回归原地了。
————
崔玉生在玉荷走?后就后悔了,可是他?这一次拼命扇打自己?的脸都没有换来她的原谅。
细数这些天,他?都干了什么蠢事啊!
余光看?见地上?撕碎的和离书,一又脚一脚的把它们踩成稀巴烂好销毁过它们的存在。
他?突然想到了钱,没错,钱。
只要他?能赚到钱,赚到好多好多的钱,玉娘肯定会回来。
现在的一切都会回归到原地。
对,没错,肯定是这样的。
因力竭不堪花折的玉荷醒来后,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辆行驶的马车中,马车虽在行驶中却感觉不到一丝颠簸,唯有窗外飞驰过的景色告诉她,先前经过了哪一处。
身体的酸软虽在方嬷嬷熟练的按摩中回了血色,只是人依旧蔫蔫得没有多少力气?。
即便共乘一车,醒来后的玉荷仍选了个离他?最远的位置,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和他?单纯处在一个空间里,都会令她感到难以言喻的恶心,并盼求着能尽快到目的地。
突然间,行驶的马车猛地停下,本就身形不稳的玉荷踉跄就要往前摔去撞到桌角时。
一只强壮有力的手已是搂过她的腰肢,用力将其?搂进怀里,低沉的声线带着丝担忧,“有没有摔到哪里。”
确定怀里人没事后的谢钧眉眼下沉,“发?生了何?事。”
“回老爷,有人在前方拦车。”
前面冲出来拦住马车的崔玉生见停下了,立马上?前,压抑着胸腔里涌动的欣喜激动,“玉娘,我有话要和你说。”
玉荷不认为除了和离以外和他?有什么好说的,只是对比于崔玉生,她更不想要和谢钧共存一室。
对于前者她是愤怒,怨恨,对于后者,她就单纯的剩下了恐惧,惊惶。
其?实连玉荷都不知道自己?为何?对他?惊恐尤甚,或许是因为他?理所当然的傲慢,不容置喙的高?高?在上?。
马车里的谢钧动作温柔的将她洒落的鬓发?别到耳后,那双浅色瞳孔里全是占有欲的警告,“去吧,记得早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