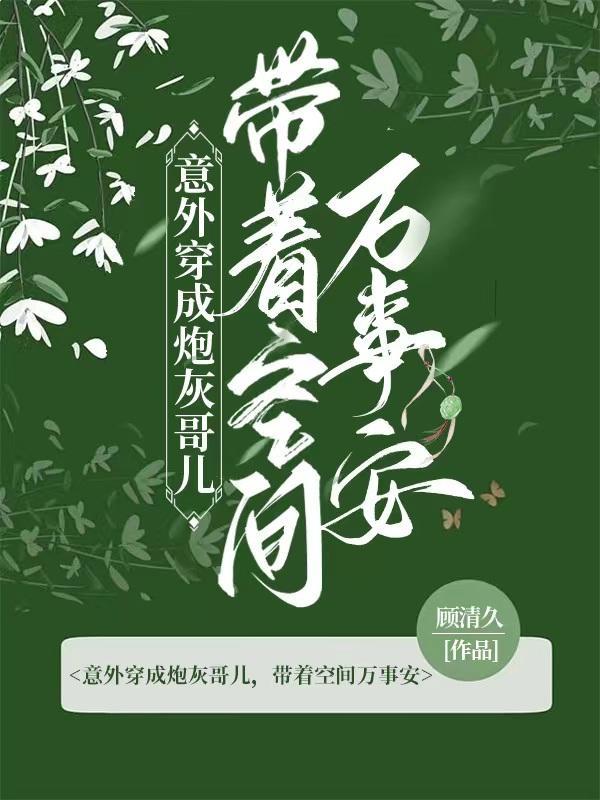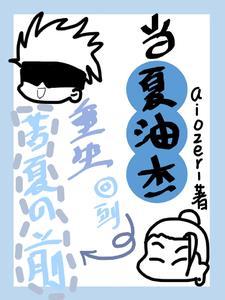零零电子书>胤礽的太子群清穿最 > 第36章(第1页)
第36章(第1页)
起初没人愿意借,还是黎百玉出面,说江南的富商都是捐银子给朝廷,而石文炳只是借,有借就有还。
如果把他逼急了,也让捐款,谁敢站住出来反抗?
毕竟他是福州将军,多年抗击倭寇,保一方平安,手握重兵。而且他手底下兵,可不是软脚虾,都是上战场搏过命狠角色。
当时黎百玉已经超越她曾经的婆家,成为当地首富,有她这一番吓唬,很多富商都乖乖借了银子。
她带头借钱,还第一个表示不要子息。听说她不要,其他商贾也纷纷表示不要。
可等到还钱的时候,石文炳又犯了难。黎百玉得知,主动上门,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如期还钱,要么跟她在一起,她替他还钱。
还明确表示,自己不要名分。
石文炳被逼到墙角,也被她的真情打动,一顶小轿把人抬进府,与她做了夫妻。
从此,福州大营再不缺粮饷,把倭寇打得落花流水,船都不敢靠岸。
“你阿玛去年的赫赫战功,有他爱兵如子,统领有方功劳,也离不开黎百玉背后的全力支持。”
胤礽最后总结道:“京官外放,通常官升一级,调回则要降。你阿玛之所以能平调回京城,主要是因为他赫赫战功,让皇上非常看重。”
大清以弓马得天下,早期重武轻文,皇上自然更看重武官,也更防备武官。
胤礽是储君,日日跟在皇上身边,他对福州那边的事如指掌,石静半点都不奇怪。
“若当真如你所说,我倒是不着急了。”有现成的正好,石静又喝下一口汤说。
黎百玉出身猎户人家,身上有功夫,是见过血,并非她原来预想的那种柔弱女子。
与汉人做生意,想必不存在语言障碍。善经商,打理石家中馈绰绰有余。在民风彪悍的福建商圈混得风生水起,对付二房一家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正是石静想为长房寻找主母。
“她性情如何?”对比过条件之后,石静只担心这个。
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幼妹,年龄偏小,性格又柔顺,很容易被人磋磨了去。
这个胤礽就不知道了:“黎百玉被抬进将军府之后,一直深居简出,不怎么露面。”
石静穿越过这么多古代社会,也见过几个女强人,比如色厉内荏卫子夫,多谋善断独孤伽罗,比如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又比如有情有义的马皇后,深知古代女强人性格千变万化,并不拘一格。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上元节宫里有灯会,南边进贡不新鲜花灯,你想过来看看吗?”说过石静关注,胤礽终于可以说说自己关心的了。
石静摇头:“我阿玛来信说他的病好了,此时应该在路上了,要赶着回家过年。他这回带了黎百玉回来,可能将她扶正。过年之后我家里全是热闹,看都看不完,就不去宫里凑热闹了。”
听前半段,胤礽眸光一黯,等听完又高兴起来:“也是,宫里灯会都没有你家热闹。你知道我是最爱热闹的,上元节我去你家看热闹好了。”
见石静无语地看向他,胤礽也觉得自己这样说有些不地道,忙改口:“我去给你撑场子。”
自家的事石静自己能搞定,哪里需要他来撑场子。那天他若是来了,全家只怕都在恭维讨好他,谁还有心情宅斗啊。
“上元节到处都乱糟糟的,你好生在宫里待着吧,别到处乱跑。”石静给胤礽盛了一碗汤,推到他面前。
记得有一回上元节,她被接回家了,他跑来找她,就被人无端扣上了一顶闹市纵马大帽子。
她问他到底纵马没有,他说没有,可苦主老娘把棺材拉到顺天府门口,自己也吊死,直接来了一个死无对证。
一顶闹事纵马,逼死人命的大帽子砸下来,想不戴都不行。
尽管被皇上压了下来,可事情闹得这样大,胤礽也算恶名在外。
那年他才十二岁。
石静也才十二岁,去哪儿都有一大堆人跟着,想做点什么都做不成。
只能劝胤礽少出宫,至少宫里有皇上,反太子党只敢捧杀,不敢闹出人命。
汤推过去,又被人推了回来,胤礽注视着她的眼睛问:“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
早知如此,他就不该等她守孝结束就急巴巴地贴上来,自讨没趣儿。
这样矫情又肉麻的问题,让石静如何回答。
她在跟他说正事,他忽然甩出这么一句,令人猝不及防。
她只是怔了一瞬,他立刻不耐烦起来,饭也不吃了,汤也不喝了,甩袖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