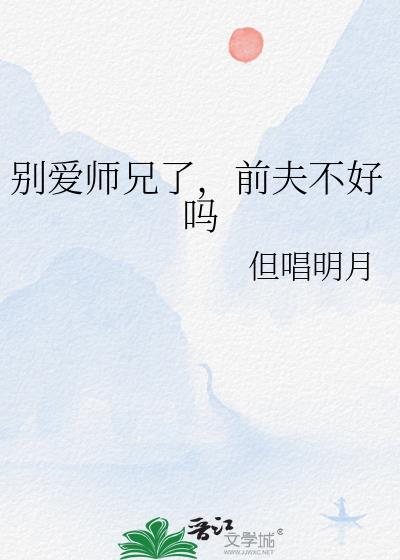零零电子书>千山月下霜 > 第4章(第3页)
第4章(第3页)
「国公爷,这小子虽然看着瘦小,但有绝活儿!」
没错。
我天生鼻子特好使。
镇国公沈难怀疑地看着我。
于是我决定给他露一小手。
我摸摸鼻子:
「国公爷早上吃了馄饨,中午吃了麻酱烧饼夹牛肉。
「中间喝了一碗药,闻着似乎是治刀伤的。
「衣服至少三天没换,上面有股硝石味道,很淡。
「我认为三天前应该发生过两军交锋。
「国公爷受了轻伤,正在养伤。
「嗯……」
镇国公来了点兴趣:
「嗯什么?痛快点。」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啊。
我清清嗓子,提高音量:
「养伤不喝酒,喝酒不养伤。
「国公爷,您偷喝了至少半坛……唔!」
话没说完,镇国公不顾形象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小点声!」
可惜已经晚了。
玄机营的「营霸」——卢神医已经气势汹汹冲过来:
「沈难!知不知道什么叫遵医嘱!
「还偷酒喝?堂堂国公爷,能不能有点出息了!
「躺好!扎针!」
卢神医在沈家军是惹不起的存在。
谁惹扎谁。
在镇国公被他捏着银针狂追三个营盘后。
我也顺利成为玄机营的新兵蛋子。
人人都说军营苦,可我却觉得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日子了。
一天三顿饭,顿顿能吃饱。
上午武教头教我们练刀。
下午文夫子教我们习字。
每隔十日,镇国公会亲自讲兵法。
就连这里的落日,都比上京的美多了。
时光日日流逝,一转眼,我仿佛被风沙摧大了。
我第一次上战场是十二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跟在镇国公的马屁股后一通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