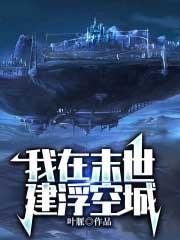零零电子书>兰台令长佩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嬴光开车上班,享受了一周出门即堵车的破交通后果断选了地铁。然后二十多年头一回坐北京地铁的嬴大少爷险些在十号线被活生生挤到灵魂出窍。此后,嬴大少爷自认这辈子无法与北京的公共交通和解,迅速收拾包袱麻利滚回了兰台。
十一月的山里不可谓不冷,似乎连藏在石罅中总是咕咚冒着泡儿的山泉都冷涩凝绝,行人耳畔只闻得呼啸着灌入的风声。
嬴光把车停在山下,趋行进山,脚下一路铺到兰台院门外的青石板路上苔衣斑斑,衬着微弱月光,寒气侵人。
好在兰台的灯是亮的,暖融融地从纱窗透出来。他学老头子的习惯,离开兰台时必定留二楼一盏灯。老头子说那是回家的灯。那盏灯孤零零地飘在视野中,却让人莫名安心。
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
兰台。
明夷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整理完两排书架,又把嬴光留给他的那一部政治学巨著看完了。他试着用圆珠笔写字,用这种笔的姿势,有些像大泽国巫师在龟板上刻字的样子,很有意思。他还对这支不用蘸墨的笔的结构起了莫大的兴趣,对一支笔好一番上下其手,拆了个七零八落后又装不回去了。
这几天除了看书,明大人也没忘在自己的兰台四处走走看看,兰台还是当年的兰台,但多了不少新东西。比如院子里的自动喷灌系统,前天下午明夷回墓里拿东西,经过时莫名其妙被突然打开的喷头洗礼了一遍,呆愣在原地硬是被水雾喷成个水鬼。还有那天他摸黑上楼,不小心一手按在开关上,“啪”的一声整个一楼灯火通明——当时明夷还以为自己变成鬼之后神力大增,可以驭火。
再比如现在四楼墙角这个白色的不知名物体,从昨天起就开始不断散发暖意,连带着整个兰台内都不冷了。三千岁的老鬼自然没见过暖气片,只知道屋内温暖,而墓室阴寒,于是更不愿离开兰台半步。
四楼安放的是嬴家人后来搜罗的藏书,大多是孤本、手抄本之类,有帛书也有线装本,都成书于明夷之后。
面对满墙不认识的,从未见过的书,明夷最初是手足无措的。他一眠三千年,除了兰台内这个凝固了一半的小世界,还不曾见过别处,也见不到别处。
嬴光拿给他的那部书,他其实看不大懂,里面将近一半的词句都不属于他的时代。
唯一能看懂的是那些关于各地风土人情的描写,那些山川河流,那些百姓和乐。
但事与时移,他并不知道三千年前某条再熟悉不过的河流早改了道,原先的名字也不知滚落何处烟尘。山倒是巍然屹立,三千年对这些沉默的峰峦而言还是太短暂,只是名字也几经更迭,落在纸上便面目全非了。
昔时有秦人迁桃源者,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明夷翻到《搜神后记》中这一篇,久久翻不过页去。
可惜他入的也不是桃源。
不过在一片冥然中,不辨八方四向,连行止坐立都不知该如何动作。
墙角有个被嬴光随手扔在那的懒人沙发,明夷读累了,便小心翼翼地靠上去——他第一次坐的时候整个人陷进去,半晌直不起身。
窗外晚景翳翳,薄暮冥冥。
这一“小憩”,便到了深夜。
……
口袋里的手机突兀地震了一下,嬴光停下摸出手机,关掉震动闹钟。屏幕上泛着冷光的白字跳动到23:00。
子时了。
农历十月十五子时,下元节。
十月望,水官解厄之日,宫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亡。山顶宫观挂起法会时才会悬挂的宫灯,隐隐有诵经声顺山风蜿蜒而下。
山道渐渐漫上清辉,将萧疏枯枝的影拓上石阶,月色凄寒。
他紧走几步进了院门,低头拢了拢风衣,再抬头时,兰台便灯火通明了——
是真正的灯火通明,连门口纱灯里的光影都变得跃动起来,所有现代照明工具,都变成了蜡烛。他蓦觉双臂一重,再看自己身上刚买的爱马仕风衣,已然变成一件绿色深衣,看上去是件官服,身份还不低的样子。
“我操……”嬴光这才想起来,自家图书馆,好像闹鬼来着。
“大人,嬴大人!”似乎有声音在叫他。
楼内跑出个长袍及地的人,拦着他低声劝回,说的依旧是陌生但能毫不费劲就听懂的古汉语:“有什么事都先放一放吧,今日兰台令史略有不适,暂不见客了。”
嬴光愣了片刻,抬眸对面前的人问道:“兰台令史……明大人?他怎么了?”
见他眼中关切,那人便道:“明大人今日又与陛下大吵一场……手下守藏史都不敢去招惹……大人初来乍到,还是不要触明大人的霉头了……”
“明大人脾气不好?”嬴光实在想象不出明夷发怒的模样。
“哪里的话,明大人脾性自然是极好的。”那人摇摇头,“只是……实在不忍见他为难了。”说完这句,他便敛容匆匆离去。
嬴光看向面前双门洞开的旧兰台,一时间心情无比沉重。
进去以后会发生什么,他再清楚不过。
兰台很静,静得能听清窗外每一片梧桐叶相互摩挲的声音。
穿着深衣行动多有不便,嬴光走不快,上楼的动作有些滑稽。
在楼上等着他的,是一个双眼无神,颓然箕坐的明夷。兰台令史向来不爱穿那沉闷的玄色官服,一袭白衣总是兀自出尘。今日却只让人觉得惨淡。他偏头对着半开的窗,不知神游何处,眼底枯然,仿佛承受着某种只要一眨眼就会支离破碎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