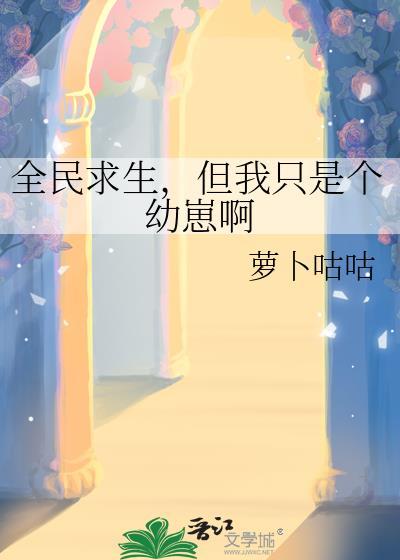零零电子书>在时光里聆听巴蜀回响作文 > 第166章 元稹 巴山蜀水间的诗魂与千年回响(第1页)
第166章 元稹 巴山蜀水间的诗魂与千年回响(第1页)
在唐代诗歌的璀璨星河中,元稹如一颗兼具锋芒与温润的星辰。他的诗既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深情决绝,也有“田家衣食无厚薄”的民生关怀;他的人生既经历过朝堂的风刀霜剑,也沐浴过巴蜀的烟雨晴岚。两次入蜀的经历,尤其是在通州(今四川达州)的困顿岁月,不仅重塑了他的诗风,更让他与这片土地结下了跨越千年的羁绊。如今,当达州人在正月初九登上凤凰山,当戛云亭的风拂过新刻的诗碑,我们仍能听见这位诗人与巴蜀的对话——那是苦难中的坚守,是诗文中的慈悲,是民俗里的传承,亦是与知己的浪漫回响。
一、元稹生平:在宦海与诗坛间行走的孤臣
元稹(—)的一生,是中唐文人“达则兼济”与“穷则独善”的典型缩影。他出身北魏宗室鲜卑拓跋氏后裔,却自幼饱尝寒门之苦。八岁那年,父亲元宽病逝,母亲郑氏带着他与三个弟弟寄居于凤翔舅舅家。这位“贤而文”的母亲,用“亲授书传”的方式为子女开蒙,在“夜课于深室之内,昼课于素屏之前”的严苛教养中,元稹九岁便能“属文”,十五岁以明经科及第,成为唐代科举史上最年轻的及第者之一。
青年时期的元稹,怀揣着“致君尧舜”的理想踏入仕途。贞元十九年(o年),他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二人自此结为终生挚友,“始相知于长安,携手于洛阳,唱和于江湖”。元和元年(o年),元稹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一名的成绩授右拾遗,正式踏入朝堂。彼时的他,锋芒毕露,在《论教本书》《论谏职表》等奏疏中直言不讳,弹劾贪腐、指陈时弊,甚至当面指责宪宗“陛下往年励精求治,今则稍怠”,其刚烈性格可见一斑。
然而,直言敢谏的代价是频繁的贬谪。元和五年(o年),元稹因弹劾河南尹房式,遭权贵构陷,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和十年(年),他因支持裴度讨伐淮西藩镇,被政敌以“结交宦官”为由弹劾,贬为通州司马;长庆二年(年),他虽一度拜相,却因卷入党争,仅三个月便被罢相,外放同州刺史、越州刺史……半生的宦海浮沉,让他从“殿前直谏”的愤青,蜕变为“渐知世事皆虚幻”的智者,而这种蜕变,在巴蜀的烟雨中尤为显着。
在文学领域,元稹的成就与他的仕途一样跌宕而耀眼。他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力求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田家词》中“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以农民的口吻控诉战乱之苦;《织妇词》里“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揭露了宫廷苛政对民间的压榨。这些诗作语言通俗如话,却字字泣血,被誉为“诗史”。
而他的爱情诗与悼亡诗,则展现了铁骨之外的柔情。妻子韦丛去世后,他写下《遣悲怀三》,“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句,道尽患难夫妻的生死深情;《离思五》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以沧海巫山喻亡妻,成为中国爱情诗的巅峰之作。此外,他的传奇《莺莺传》以细腻笔触描绘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悲剧,为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提供了蓝本,可见其文学创造力的多元。
这位集斗士、诗人、情人于一身的文人,注定要与巴山蜀水相遇。当他第一次踏上蜀道,当他在通州的茅屋里病中惊坐,当他在锦江畔与薛涛唱和,命运早已为他与这片土地写下了不解之缘。
二、初入东川:梓州的监察御史与诗酒风流
元和四年(o年)春,岁的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这是他与巴蜀的第一次相遇。此行的官方任务是查办前东川节度使严砺的贪腐案,而这场看似普通的公务,却成了他人生与诗风的重要转折点,更让他邂逅了与薛涛的一段诗坛佳话。
蜀道上的风霜与诗行
从长安到梓州,元稹走的是“骆谷道”——这条穿越秦岭的古道,以险峻着称,“七盘九折,猿啼鸟怨”。他在《使东川》组诗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旅程:行至骆谷时,恰逢春雨连绵,“栈云栏月愁忙杀,明日骑驴复西去”,道尽旅途的奔波;过青山驿时,见壁上前人题诗,“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顿生“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时空之叹;抵褒城时,正值花期,“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借赏花醉酒排遣羁旅的孤寂。
这些诗作不同于他早年的讽喻诗,少了锋芒,多了对自然与人生的细腻感悟。在《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夜对桐花,寄乐天》中,他写道:“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怨澹不胜情,低回拂帘幕。叶新阴影细,露重枝条弱。夜久春恨多,风清暗香薄。”月光、桐花、夜风,在他笔下交织成一片朦胧的愁绪,这种“以景寓情”的笔法,正是蜀地烟雨对他诗风的最初浸润。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梓州的铁面御史与民生情怀
抵达梓州后,元稹迅投入查案工作。严砺在任期间,曾借“讨伐刘辟叛乱”之名,大肆掠夺泸州、合州等地百姓的田宅,甚至擅自增加赋税,“没入百姓产业八十余户,税外加征钱帛数十万”。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直到元稹到来,才看到希望。
这位年轻的监察御史展现了惊人的魄力与细致:他逐一核查严砺的卷宗,传唤涉案百姓与官吏对质,甚至亲自前往被掠夺的田宅实地勘察。在《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中,他详细列举了严砺的条罪状,包括“擅收没百姓田宅”“税外加征”等,字字确凿。最终,朝廷下令为户百姓平反,归还田宅,严砺虽已病逝,其下属也均被追责。此事过后,“东川百姓歌舞于道,呼元稹为‘元青天’”。
查案之余,元稹深入了解蜀地民生。他在《估客乐》中记录了梓州商人的生活:“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通过商人的视角,展现了蜀地商业的繁荣与百姓的生存哲学。他还走访乡村,见农民“终岁服劳役,不得避炎凉”,写下《农父》一诗:“农父冤辛苦,向我述其情。难将一人农,可备十人征。”这种对底层的关怀,为他后来在通州的作为埋下伏笔。
与薛涛的诗坛邂逅:锦江畔的浪漫回响
在梓州,元稹与蜀中才女薛涛的相遇,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诗坛佳话。薛涛出身官宦之家,自幼随父入蜀,后因父亡沦为乐伎,却以诗名动一时,与韦皋、武元衡等蜀地官员多有唱和,人称“女校书”。
元稹早闻薛涛诗名,抵达梓州后便主动邀约。二人在锦江边上的浣花溪畔相见,薛涛以《池上双鸟》相赠:“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忆将雏日,同心莲叶间。”诗中以双鸟喻知己,含蓄表达了倾慕之情。元稹则回赠《赠薛涛》:“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五云高。”将薛涛与卓文君并提,赞其才思敏捷、文章华美。
此后的数月里,二人时常在梓州的亭台楼阁间唱和。薛涛的诗清丽婉约,如《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元稹的诗则豪放深情,以《寄赠薛涛》回应:“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五云高。”他们的唱和之作,既有对时局的感慨,也有对彼此才华的欣赏,更有一丝朦胧的情愫在字里行间流淌。
薛涛曾特制“薛涛笺”相赠——这种以芙蓉花汁染成的桃红色小笺,小巧雅致,正适合书写短诗。元稹收到后,在笺上写下“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足见珍视。这段情缘虽因元稹离蜀而终,却为蜀地诗坛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成为锦江畔一道永不褪色的浪漫风景。
元和四年(o年)冬,元稹完成使命离蜀,他在《东川别舍弟楼》中写道:“阶前春色浓于酒,牖外秋声碎似珠。今夕秦天一雁过,去年蜀地百花开。”字里行间,已流露对蜀地的眷恋,更藏着对这段诗酒情缘的不舍。他不会想到,五年后,他将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且是以一种更为困顿的方式。
三、再贬通州:达州的困顿岁月与生命觉醒
元和十年(年),元稹因卷入“王叔文集团”余党案,被贬为通州司马,这是他第二次入蜀,也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通州(今四川达州)地处川东,在唐代属偏远之地,“地多瘴气,民少读书,俗尚巫鬼”,而正是这片土地,让他完成了从“愤青御史”到“智者诗人”的蜕变。
赴任途中的绝望与坚守
从长安到通州,路程比赴梓州更远,且多为荒僻之地。元稹出时便身患疾病,“病骢犹向瘴江行”,一路颠沛流离。他在《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中描述:“蛮地无霜雪,逐臣稀物役。唯恐远归来,表是身非实。”可见其内心的绝望。
行至青山驿时,他想起五年前出使东川时曾在此停留,物是人非,感慨万千,写下《青山庙》:“惆怅青山路,烟霞老此人。只应松自立,而不与君春。”诗中的“青山”既是实景,也是他对命运的隐喻——即便身处绝境,也要如青松般自立。
六月,元稹终于抵达通州,迎接他的不是官舍,而是“荒祠古柏”。他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写道:“通之地,湿瘴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杂獠。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初到之时,他只能借居在州河对岸的开元寺,“僧房破落,四面通风”,夜晚听着“獠人”的歌声,思乡之情难以抑制。
更让他痛苦的是疾病。通州的湿热气候让他患上疟疾,“一卧十余日,头眩不能起”,甚至一度濒临死亡。他在《别李十一》中写道:“闻道阴平郡,翛然古戍情。戍迥山形断,河穷地势萦。烟霞潘岳鬓,林壑谢公情。今日龙钟人共弃,愧君犹遣慎风波。”字里行间满是病中的凄凉。但正是这场大病,让他开始反思人生:“病中知世事,身外即浮云。”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戛云亭上的精神突围
在通州的第三年,元稹的生活稍有安定。他在州河南岸的青爱山(今翠屏山)选址,亲自督导工匠修建了一座茅屋,取名“戛云亭”。“戛云”二字,取自“戛然独立于云端”之意,既是对亭子地势的描述,也暗含着他的精神追求——即便身处蛮荒之地,也要保持人格的独立。
戛云亭虽简陋,却是元稹观察通州、思考人生的“精神高地”。他常在此登高远眺,俯瞰州河如带,远眺大巴山如黛,写下《戛云亭》一诗:“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但有浮云横碧落,更无幽恨到黄尘。”诗中没有贬谪的怨怼,只有对天地广阔的感悟,这种“越苦难”的心境,与他早年的愤懑形成鲜明对比。
在戛云亭,他还完成了《连昌宫词》这篇长篇叙事诗。诗中借连昌宫的兴废,回顾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兴衰,“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通过今昔对比,反思安史之乱的教训。这种“以史为鉴”的视角,正是他在通州沉淀后的思想升华。
除了作诗,元稹还在戛云亭接待来访的友人。当地学子听说这位“京城来的诗人”博学多才,常来请教,他总是耐心讲解,甚至捐出自己微薄的俸禄,为学子购置书籍。有一次,一位老秀才来请教《诗经》,他与之谈至深夜,临别时赠诗:“衰容不称君,清风满敝庐。”这种与百姓的亲近,让他逐渐融入通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