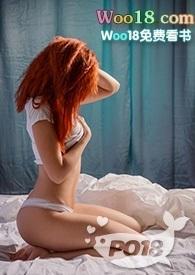零零电子书>圆圆记事+番外 > 第128章(第1页)
第128章(第1页)
说着就坐到陈姨妈身边打量她。
没想到一年没见,自己这个正头娘子反而容姿焕发,脸上肉都多了起来。
三十多的人了,不擦粉都这么白净。时至今日他在看这张脸还是要赞叹一句自己当年眼光好。
只是年轻的时候喜欢冷美人,娶回来了又觉得玩着不痛快,不像外头的女人,在床上让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
陈氏腰板儿直,心思也淡,怎么弄都不喘,跟她做夫妻做久了就没意思。
现在千帆过尽,宁文博又觉得冷美人别有滋味儿了,太软了玩着也不够劲。
宁文博眼睛扫在陈姨妈胸口屁股上,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
陈姨妈跟他怎么也有过新婚燕尔的时候,看他的眼神心里就有数,当下就有点儿想吐。
以前宁文博至少生得好,现在都吹气成馒头了!
再说老太太尸骨未寒,当儿子的还想着下头那二两肉爽快,这还是人吗?自己以前怎么就看上这么个臭鱼烂虾!
陈姨妈看着宁文博摸过来的手,忍不住回忆起以前跟他花前月下被翻红浪的日子,当时样样都好,只恨日头太短。
后来她试遍了克夫的招数,都没屁用!
老太太在的时候老不让在脸上擦胭脂,说擦在颧骨上克男人,昨晚她顶着胭脂睡了一晚上,怎么今天这死人还活跳跳的!
陈姨妈抬头又看了一眼宁文博,腰一弯吐了一地,她常年喝药,吐出来的味道不怎么好闻,就是自己闻着都皱鼻子。
杜嬷嬷急急忙忙地拿了香枣过来给她塞鼻子,又叫人进来打扫。
宁文博伸在陈姨妈背上的手就慢慢退了回来,难得多了一点儿人性,担忧地着问她:“身子骨怎么还么养好,最近吃的什么药?早上吃的什么饭?”
陈氏当了一路流民,身子骨早就坏了,嫁到宁家之后更是三天两头生病,以前两人浓情蜜意的时候,宁文博总是要把她揽到怀里拍着背问有没有事。
现在他嘴里还说着关心的话,但陈姨妈心里已经没有一点儿温情在了,甚至连以前那种亲密无间的时刻都不能让她有丝毫动容。
王老太太要冲两回喜保命,成了全城茶余饭后的谈资。
街上卖豆腐的说:“蓝家不愧是书香门第,把女儿教得这么孝顺,竟然肯一切从简嫁过来给老太太冲喜。”
磨镜子的老头儿提着豆腐道:“这有什么,读书人知廉耻。要我老子看,还是段家更胜一筹,段大老爷也就是个富家翁,多讲究排场啊,还不是提前让嫁过来了,听说他们家本来想把宁大奶奶留到十八岁再出门子!”
不管怎么说大家又能搓一顿了!
段圆圆走在二房的路上,听着罗衣打听回来的消息就想笑。
她爹和祖爷本来就打算让她十六岁嫁出去啊,她等得但宁宣等不得。
戏剧
大房和二房虽然是同一个宅子隔开的,但中间的距离不算短。
十二月天都冷得人发抖了,坐着干烤火脚还是冻得慌,静下来体会一下就觉得骨头缝里都是冰渣子。
段圆圆想自己走走,所以没要小轿子,戴了护耳和披风就跑了。
——这种出门的机会又不是天天都有,而且就这几步路嘛!
结果几个人一走就二十多分钟,走了这么久也才走到大门口,要是老太太被藏在最里头,那又得再走二十多分钟。
青罗想到这个脸就绿了,天这么冷要是把姑娘冻坏了怎么办?她又折腾着要叫轿子过来。
段圆圆还是没同意,她上一次出宁家宅子是跟宁宣一起去认识外头的铺子,但功课都需要温习啊,久了不出去现在纸上的东西她还记得,怎么走到那里去已经模糊掉了。
宁家这个宅子她也就认识后院的样子,前头各房住了什么人,办什么事那都是一知半解。
段家是乡野小民,她在里头是跑惯了的,现在一步一步走在青石地板上,段圆圆才知道,原来从她的屋子走到大门口要这么长时间。
门外是新的世界,她都没好好看过啊!
卖豆腐的卖烤红薯的卖寒冬饮的,热气腾腾的喧哗声都很别致。
段圆圆瞧着稀奇极了,这跟段家宅子附近的田野景色完全不一样!
偏门上还有丫头婆子叫住卖针头线脑的婆子扯手帕。
段圆圆看到杜嬷嬷养的那个跟她女儿有几分相似的小姑娘也在,她穿着白绫袄儿和寿菊纹路的棉裤子蹲在地上,跟另一个小姑娘买伤心凉粉和莲子糊吃。
小孩子养得结实,穿暖了就不怕冷,这么冷热乱着来也活蹦乱跳的。
杜嬷嬷看段圆圆瞧着小丫头了就笑着跟她说:“米儿跟那头那个卖凉粉莲子糊的两婆孙有点儿缘分。”
之前那个小姑娘家里活不下去也是叫卖了的,只是她长得不怎么样,最后没卖出去,她娘老子还给人牙子赔了二升米钱。
实在没办法了,她外婆有空就带着她上山捡山货,存够了再拉着板车出来卖,小姑娘记得这条街有钱人多,都是做生意的,也不怎么赶人,就把外婆往这里带,回回都要在墙外头叫:“米儿,米儿。”
门房打都打不走,这又是普通老百姓不好动粗,让宁宣知道了少说也是一顿班子。
最后门房只能叫米儿出来。
米儿也记得一张床睡了几个月的小伙伴,就带着宅子里的丫头们出来买东西,好歹能糊口不让娘老子再把这小姑娘卖了。
“也算是共患难了。”说完杜嬷嬷又感叹:“这婆孙两个力气跟小花差不多,一日能推百多斤的东西走街串巷去卖,中午不吃饭,自己摸个院子要碗井水啃馒头都还有劲儿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