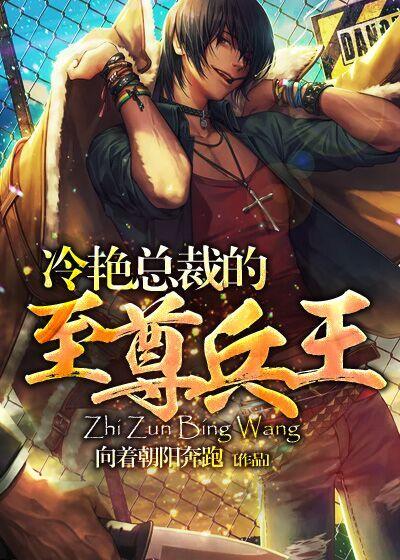零零电子书>熊猫穿越异世娶夫郎+番外 > 第757章(第1页)
第757章(第1页)
大人,需要小的喊一声吗?
张舒越:“……”
不喊难道留着人在考场里头过年吗?
张舒越说他亲自喊,他咬牙切齿到了十九号舍外头,对着考舍踹了一脚。
声响巨大,整个考场都听见了。
白子慕以为出了啥事儿,吓得一个踉跄起来,从小门伸脖子一看,大家陆陆续续往外头走。
哎呀,原来是是时辰到了。可诗还没写呢!不管了,以前老师说了,试卷最好不要留空,那样不好看。
这会儿衙役正在第一排收卷,还没收到他这儿,还是赶紧写两句然后赶紧走吧!
张舒越眼睁睁的看着白子慕匆匆写了几字,然后东西呼啦啦一收拾就从自个跟旁跑出去,看都不看他一眼,彻底无力再气了。
三月底,楼县令亲自给张舒越来信,信上写了,师兄,我儿子和学生这次要参考,宇杰无事,但我那学生和沈家有些龌龊……还望师兄出手相帮。
初一白子慕前去衙门报名,果不其然,他前脚走,后脚那名字便被划了。
张舒越脸色直接冷了下来,当着知洲严信章的面直接问他,为什么划了这人的名?
严信章没料到他会过来,而且是一过来就问白子慕的登记表在哪里。
他怎么会知道白子慕这个人?
那不用问,肯定是楼倡廉说的。
张舒越估摸着是要护着这人。
于是严信章便打哈哈,说划错了划错了。
怎么可能会划错,不过就是借口罢了,但没必要说重挑破脸,张舒越便没说旁的,只淡淡瞥他一眼:
“此人乃我师弟门生,本官也不是糊涂之人,严大人,小一辈的恩怨,当是小一辈的事,你公私不分,是不是不太好啊?”
严信章当即白着脸认错,说是他糊涂了,下次万万不敢。
晚上回府,傅君然过来,问咋的样?
严信章说这人怕是动不得了。
怎么动不得?
严信章说:“我原以为大人和楼倡廉关系不合,大人不会出手,但如今看来,倒是我想茬了,也对,他们即使关系再不合,但到底师出一门,大人断然不可坐视不理,咱欺压白子慕,那便是在欺压楼倡廉,这也是在打大人的脸啊。”
“岳父,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吗?”傅君然怒气腾腾:“这人打了我表哥,女婿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严信章:“这姓白的打过沈正阳?”不应该啊!据消息说这姓白的是第一次来府城啊!
“是。”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十月。”傅君然眼神阴沉的说。
当初沈正阳敢公然和白子慕抢东西,白子慕自是不会让他毫发无损的从平阳镇走出去。
若是抢旁的,白子慕都不至于那般气,可抢他孩子的口粮,他如何能忍?
孩子已经皮包骨,就等着这一口呢!